以“荒谬”反击荒谬
人生没有希望但并不包含绝望。所以,要活得真实而不虚伪,就必须坚守下去,并不是不愿迂回,而是没有退路可走。这是加缪荒谬论中的一个有名的论点。
全书分为两个部分,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叙述,从莫尔索的母亲去世开始,到他在海滩上杀死阿拉伯人为止。这种叙述毫无抒情的意味,只是莫尔索内心的自发意识,因而从读者的视角看,他叙述的接二连三的事件、对话之间似乎没有很强的联系,给人以一种不连贯的荒谬之感,因为别人的动作和语言在他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,是不可理解的。确实的存在只有大海、阳光,而大自然却压倒了他,使他莫名其妙地杀了人: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我感到天旋地转。海上泛起一阵闷热的狂风,我觉得天门洞开,向下倾泻大火。我全身都绷紧了,手紧紧握住枪。枪机扳动了
在第二部分里,牢房代替了大海,社会的意识代替了莫尔索自发的意识。司法机构以固有的逻辑,利用莫尔索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件,把被莫尔索构造成一种他本人都认不出来的形象,即把始终认为自己无罪、对一切都毫不在乎的莫尔索硬说成一个冷酷无情、蓄意杀人的魔鬼。审讯不调查杀人案件,而是千方百计把杀人和他母亲之死及他和玛丽的关系联系在一起。
大部分人总是表里不一,他们做的往往并非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。他们都有一种群居意识,惧怕被疏离与被排斥,惧怕孤单无依靠。但是莫尔索却有意无意地要跳出这个世界的既定模式,保持和芸芸大众的距离,完全遵照内心本性,做一个冷眼旁观、我行我素的局外人。这种局外人体现在几个方面。
首先是情感生活上的局外人,今天,妈妈死了。也许是昨天,我搞不清。这就是小说惊世骇俗的开篇。丧失亲人的打击无疑是沉痛而惨烈的,可是他却以极其平静的口吻轻描淡写地叙述,自始至终都没有流过半点哀伤的泪水。女友玛丽问他是否爱她,他绝对不肯巧言令色来搪塞女友。邻居殷切表示想与他交个朋友,莫尔索却回答做不做都可以,一副无所谓的态度。
其次是工作,工作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、获取荣华富贵的重要途径。基督徒认为工作是上帝赐予的使命,必须要严肃认真地对待。可是,当老板提出要派莫尔索去巴黎设置的办事处工作时,他却说:人们永远无法改变生活,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。
最后是死亡,他错杀了那个阿拉伯人之后,无论是在狱中,还是在法庭上的审判声中,他保持了一贯的冷漠态度。人们的言辞无法引起他太大的关注,周围微末的事物却紧紧攫住了他的心。我听见椅子往后挪的声音,我看到好些记者都在用报纸给自己扇风,尽管挂着遮帘,阳光仍从一些缝隙投射进来面对人们义正辞严的谴责,他继续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,完全没有为了保命而讨好大众的媚态。在得知不公正的死刑强加于身后,他顽固地认为自己曾经是幸福的,现在依然是幸福的,我希望处决我的那天,有很多人来看热闹,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。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天性,但是莫尔索却等闲视之,不以为意,摆脱了死亡对他的困扰。
莫尔索的种种怪诞行为好像难以理解,但事实上,他才是有着深沉本真追求的人。死亡前夜,他第一次敞开心扉,他觉得自己过去是幸福的,现在也是幸福的,他至死都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,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荒谬,但至死幸福。加缪说,莫尔索远非麻木不仁,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,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。他早已洞悉这个世界的荒谬,他意识到世界没有意义,没有出路,认识到世界对于人的种种欲望漠不关心,认识到人同世界特别是人同社会这种不协调乃至对立的关系。他热爱自然,渴慕自由,珍惜每分每秒,完全靠着自己现实的理性与实践精神支配着一切行动。
他并非对母亲没有感情,只是不愿意强迫自己为了做戏而哭天抢地,昭告世人:我很伤心,尽管形式上他的表现不符合孝子标准,可还是在灵魂深处敬爱母亲的。
本书写于二战期间,这个时期,西方世界正处于战争的恐慌之中,人们对社会充满迷惘,精神没有归宿。莫尔索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,他们孤独、痛苦、冷漠,但又不甘于被现实的世界如此凌迫,于是他们变成了世界的局外人,以冷漠来反抗生活,却最终未能逃脱在命运面前的惨败,悲剧是注定的,但蔑视悲剧的态度却让他成了一名挑战荒谬的英雄。
在既定的社会准则下,人的命运是未知的,是不可控地被裹挟着的,要么异化,要么被审判,于是,想做个真诚地忠于内心的人还是做个随大流的人,是至今为止,很多人都面临的选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每个人都是莫尔索。
以荒谬反击荒谬,这正是《局外人》主人公莫尔索的思想,当然也是作者阿尔贝·加缪的思想和创作意图。
本文地址:www.hzydhh.cn/html/262345.html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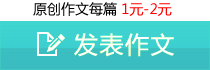


猜你喜欢: